马上注册,结交更多好友,享用更多功能,让你轻松玩转前线论坛。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,没有账号?中文注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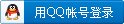
×

正如歌里唱的,“回不去的是故乡”,我的故乡不是牡丹江。既然上一篇写摩洛哥的文章里提到烟台,那就写写我回不去的故乡吧。回不去,不是说真的到不了那个地方,而是内心的惆怅,“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”的过往。烟台三面环山、北面临海,自古福地也,有一个区就叫福山区。烟台历史悠久,古称登州、莱州。牟平的养马岛,据说因为秦始皇的军队在那儿圈养过战马而得名;明洪武三十一年(1398年),为防倭寇,在今烟台山设狼烟墩台而得名;1861年开埠,成为清朝北方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;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,1897年烟台乃至整个胶东被德国强占;1915年1月18日,日本趁一战西方国家无暇东顾,向中国提出荒谬的“二十一条”,企图独占胶州;1919年6月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巴黎和会,却被要求签署丧权辱国的《凡尔赛和约》,“和约”规定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交给日本,中国政府未签字。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,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线……说起烟台,烟台苹果、莱阳梨最为著名,近年又有了大樱桃。烟台苹果分国光和金元帅两个品种,国光虽然好吃,但个头儿小,卖相不好,后来被杂交品种富士替代了。樱桃是这些年才有的,我小时候没听说烟台产樱桃。十几年前有一次坐飞机去烟台,从莱山机场出来,看见道边全是樱桃树。其实烟台不光出产水果、海鲜,还有许多名牌产品,如三环铜锁、飞轮罐头、北极星钟表、张裕葡萄酒,还有后起之秀飞蝶牌小轮自行车,都很著名,只是现在除了张裕,其它企业都不景气。父亲是莱阳人,按理说我的故乡应该是莱阳,但我出生在烟台,当时烟台是大地区,莱阳、海阳、威海、荣成、文登、蓬莱等县都隶属烟台管辖,后来有的才升为县级市。我在烟台长到快七岁,随父母移居北京。初到北京,住在百万庄建委大院(现建设部大院),又是七年。活了半辈子,搬过七、八次家,有人说每一个家都是一个人生驿站,但我梦见的人生驿站,只有烟台的德仁里和北京的建委大院——其实我很少梦到家。我父亲是“抗美援朝”战争之后驻扎烟台的,经人介绍认识了我母亲。结婚后,他又被保送上军校,毕业当教员留在北京。用他的话形容当时烟台之小就是,“点一支烟可以从东头儿走到西头儿”。当然这是夸张,不过我小时候的印象,从东口子到西边消防营,满打满算也不超过十公里,再往外就是农田了。现如今,“东口子”已名存实亡,高速路直通威海,不留神一脚油就到了养马岛;西边通往蓬莱,从前要背上干粮起早贪黑走一天半的路,现在也就一个小时的车程。2003年3月非典前的某夜,又梦见烟台:我在一条通往海边的胡同里奔跑,阳光灿烂,前面的大海蔚蓝,有一艘白色巨轮;两旁建筑向后掠去,我却怎么也跑不到海边。第二天,晓丹妹妹就打电话,说请我去青岛拍一些照片,而在青岛住的宾馆,就在老人石附近海边——生活中就有如此难以解释的巧合。还有一个真实却像梦境的回忆:我大概三、四岁的时候,有一天跟妈妈去同事家串门,那位大姨住在东口子金沟寨一带的农村,还是在山上。下午我在村里和小朋友玩儿,他们对我很友好,教我逮蚂蚱,还给我摘果子吃。吃完晚饭,天已经黑了(应该不很晚,因为太晚就没有公交车回家了)。大姨拿着手电送我和妈妈下山,走在小路上,周围全是萤火虫!远处海面映着月光——深蓝璀璨的夜空下,月光、矮树、虫鸣、萤火虫、碎银子般的波涛,这种情景,只有在宫崎骏的动画片里才能看到……

23岁那年,我去沈阳参加上戏专业考试后,经大连乘船到烟台,把妈妈接回北京。到的第二天,适逢我生日。上午,妈妈带我到大马路买鱼买菜,并专程到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德仁里,在7号院门口合影留念(摄于1987年4月21日)

妈妈抱着三岁的我。背后是姥姥家房子,妈妈旁边是无花果树。照片是父亲的老战友张伯伯拍的,他离休前是《青岛日报》副总编,当时是记者,我的摄影启蒙者(摄于1967年)

慈祥的姥姥坐在海沿儿,远处是烟台山,她背后是小时候住过的洋楼(摄于1989年10月)

从大马路通往海沿儿的这条路,如今在现实和地图上已经消失了,我也忘了叫什么。这条路上有市武装部和我曾上过的幼儿园。那位行人旁边的小楼是姥姥故居的外围(摄于1989年10月)



烟台海岸街(摄于1989年10月&2000年10月)

十字街农贸市场。这条街与大马路交汇处,是一座天主教堂(摄于1989年10月15日)
离开烟台快五十年,曾返乡多次,但每回一次,就感觉陌生一点,那些承载当时记忆的人和物都不复存在,我对现在的烟台已经没有多少好感和眷恋。我没去过日本,却总感觉儿时记忆中的烟台就像日本某些海滨小城,函馆、镰仓、伊豆、小樽,它本也可以建得那样诗意、美好,而现在跟全国千篇一律的中小城市无异,俗气且浮夸,偶尔在深藏的角落才能看到一点往昔的韵味。烟台横竖就那么几条街,就那么大块地儿,因此半个世纪前的烟台在我的记忆里是深刻的、丰富的、鲜活的,现在一回想起来,就像放无声老电影一样,连绵不断又杂乱无章。烟台城清末时主要集中在海防营、所城里,后来又发展到烟台山周边,跟北京四九城儿一个意思,就是我爸形容一支烟的范围。住城外的北京人会说“进城”,烟台人则说“去街里”,有一种即时的亲切感。姥姥家住的南山路,与“街里”的地理关系相当于北京三里屯到二环东四十条桥,当然要近得多,沿二马路或三马路往西走,不一会儿就到了街里。姥爷经常用小车推着我,到二马路转盘一家小铺儿喝馄饨,八分钱一碗,烤饼二两粮票六分钱;从转盘往北不远,就是张裕公司大门,路口有个公共浴池,姥爷经常带我去洗澡;从张裕和浴池的街口往东,就是大马路,一直能到虹口路,当时再往东就是海军炮校了,属于军事管制区;从虹口路折向南是二马路东端和东花园,花园里有一个神父墓和一位革命烈士的墓,再往西走就又回到南山路了,方圆一公里多点儿,我小时候的主要活动范围差不多就这么大。隔三岔五,姥爷也会推着我去海沿儿,或者从三马路向西,沿着东关街、所城里,到动物园消磨时间。动物园很小,也没多少动物,我最爱看猴和海豹,海豹池子半个篮球场大,圆的,几只海豹在里面不停地转圈儿。我看动物的时候,姥爷就在一旁抽烟、看报纸。稍大点儿知道,过了所城里,西关街路北一个高坡上的小院儿,是太奶奶和三姥爷的家,但姥爷从来没顺路带我去看看他妈和三弟,只有年、节才去。太奶奶瞎了,每次去她都要捧着我的脸,用干枯的手不停地摩挲,甚是可怕,所以平时不去也好。现在想来,姥爷经常带我去动物园,也许是为了平日里离母亲近点儿。太奶奶比毛泽东早去世三天,1976年9月,我比别的同学早戴两天黑纱。南山路是城东一条南北向的路,从南山根儿到海边,贯穿四马路、三马路、二马路、大马路。由于烟台的马蹄铁地形,地势南高北低,且有起伏,市里的毓璜顶是一个制高点。在三马路到二马路之间,有一条东沟路通东花园,还有从南到北并列的德仁里、德寿里、德安里三条里。里与胡同的区别在于,胡同是通的,里的一头儿是盲端。姥姥住德仁里最里面的1号,院里还有袁爷爷家和大光家,姥姥与袁家、大光家都不太对付。袁爷爷以前是小资本家,老两口和一个女儿、俩儿子,日子过得挺细致,待人很温和;大光的爸爸好像是个小干部,妈妈在街道工作。我记忆中,姥姥和袁家的矛盾跟养鸡有关,姥姥养了几只乌鸡,从时间推算,可能是为了给我妈和舅妈坐月子补充营养,我妹和表弟相差不到一岁。临时砌的鸡窝虽然紧靠我家房子,却就在袁家门口,人家肯定不乐意。有一天早晨发现鸡全丢了,姥爷和舅舅都认为是黄鼠狼拖走的,但姥姥说头天晚上听见咣咣咣的敲击声,认定是袁婆子敲鸡窝先把鸡吓傻,鸡不会叫了,然后再捉,“黄鼠狼子不会这么悟亮”。长大后知道黄鼠狼是怎么偷鸡的,简直聪明到家啦,所以也认为姥姥冤枉了人家。我倒没什么禁忌,见了袁家人,该叫谁叫谁,袁爷爷进进出出,也经常摸摸我的头。院里有棵无花果树,树的大部分枝杈伸到袁家房顶。秋天,袁家小儿子永福叔就给我摘无花果,还到屋顶捡熟透了的无花果干儿。街壁儿3号院住着桑姥姥和另外两家。桑姥爷满脸麻子,人高马大,真正山东大汉的模样;桑姥姥跟我姥姥年龄差不离儿,可是门牙掉了,就显得老气许多。桑姥姥家人丁兴旺,几个儿子、闺女,都长得很壮实,像他们的爹。桑姥姥养了几只鸡,每天母鸡咯咯哒地叫时,不管我在干什么,都会说一句:“桑姥姥下蛋了”,姥姥便笑。回头见了面,姥姥就问桑姥姥:“你今天下了几个蛋啊?”桑姥姥瘪着牙回骂,俩老太太笑作一团。5号院住着郭姥姥、宋奶奶等三家。郭姥姥即使年纪大了、穿着朴素,也是干干净净、体体面面的样子。年轻时一定很漂亮,她儿子就是最好的佐证,当时只觉得郭舅舅跟我舅舅一样帅,后来看电影才知道他长得特像唐国强。德仁里一共有三个高门大院,7号院是其中之一,好像也是唯一最标准的三进四合院,倒座、前院、影壁、垂花门、正院、东西厢房、正房、耳房、过厅、后院、后罩房一应俱全。因为院子太大,人多进出不方便,后院在西边夹道另开了一个门。之所以对这个院子如此熟悉,是因为我妈妈在7号院有间房,虽然只是一间倒座房,却有二十几平米,举架很高,前后两个大窗,窗台足有一尺多宽,夏天我经常铺个凉席在窗台上睡觉,可见这房子墙有多厚吧。7号院西边是个空旷的大院子,还有后门通到德寿里。院里只有一排房,住着一户人家。后来我猜想,那个院子可能是7号这家大户的偏院,垛粮食、养大牲口之用或是预留地。1976年回烟台,那个院子已经拆了,盖起三排二层简易楼,可想而知那个院子曾经有多大。7号对面,东边4号院也是大门大户,而且有东、西两个跨院。东边是个四合院,就一进,东厢房是我发小儿大路路家,南房是王桂枝家。桂枝姨是我妈的小学同学,翘鼻子,头发自来卷儿。她老公是地质工作者,很少在家,所以生孩子比我妈还晚,儿子跟我表弟同龄;西跨院也挺大,住着哑巴及另外两三家。哑巴两口子都哑,大儿子也哑,姥姥特怜惜哑巴家俩孩子,小的是闺女;还有一家,妈妈和女儿都挺漂亮,我和那女儿还有点儿小故事……西边6号院是大姑家的院子,住户特别多,至少七、八家。临街住的是后搬去的简宁家,我跟他也是好朋友。若干年后,在黄亭子五十号酒吧认识诗人简宁,第一句话就问:“你是哪儿人啊?” 后来才知道,简宁是他的笔名。小时候,每个社区都会有一个傻子,反正电影里总这么演,现实中似乎也是如此,住在建委大院时,有大惠和压板条儿。烟台管傻子叫彪子,德仁里也有一位,女的,家里大人让我叫她“大姑”,如果顺着我妈、舅舅这边,按理应该叫“大姨”才对呀。大姑上过大学,清华大学,五十年代末,因为政治原因和恋爱问题疯了。那时大姑应该三十岁出头——反右时她大学没毕业,我记事儿大约是1967、68年——可相貌却似半百之人,头发花白凌乱、破衣烂衫,看人总是直勾勾的。胡同里有的孩子总欺负她,她全不理会。姥爷、姥姥从不许我对大姑不恭,他们待她也很尊敬。投桃报李,大姑对我非常好,总是笑盈盈的,经常送我蚂蚱什么的。有一年我养蚕,大姑每天上山拾草都给我带回新鲜桑叶。据说大姑家的院子全是她家的,后来住进多家外人,她家只住几间南房。我经常去大姑家,因为穿过大姑家堂屋和后院,就到了南边的东沟路,姥爷每天去那条街的垃圾库倒垃圾,有时我便偷偷从大姑家跑过去,提前躲到垃圾库门口吓唬姥爷。大姑的家人我印象很模糊了,只记得她有个弟弟,二十岁左右的样子。

南山路与三马路十字路口。右边是奇山教堂,正前方是南山路副食店,旁边正在拆的二层小楼是原先舅舅家,小楼背后是一个果园(摄于1989年10月15日)

三马路东头,前面通往市气象局和市福利院。福利院周围是大片桑林,再往上就是连着东口子那边的山了(摄于1989年10月15日)

正在拆的德仁里。挂路牌的房子是王姥姥家;右边是南山路小学,以前是基督教会办的学校,二层的建筑呈口字型,南侧还有一个八角楼。我曾经在《老照片》杂志上见过这两座建筑的老照片(摄于1989年10月15日)

小时候觉得德仁里又宽又长。我站的地方是东端,原来是个自来水井,右边就是姥姥家1号院,左边是2号院(摄于1989年10月15日)

站在原先姥姥家屋里拍残垣,感慨万千。原先分成三间,可能后来的住户把隔断打通了。房子虽不如7号院的讲究,但也是三七墙(摄于1989年10月15日)

站在姥姥家屋顶平台拍街壁3号院。四间北房(右侧)就是桑姥姥家,原先院里没有搭建的小屋(摄于1989年10月15日)

德仁里7号院大门口,电线杆后面的就是原先妈妈的房子。那道影壁前,有姥爷、姥姥搬去后盖的煤棚和鸡窝(摄于1989年10月15日)

站在妈妈房子隔壁的屋子里拍整个7号院,垂花门早已经拆掉。请注意墙的厚度,早先盖房,真是百年大计(摄于1989年10月15日)

德仁里6号院。那位拾荒老人站的地方,就是原先大姑家的房子(摄于1989年10月15日)
在烟台的那段童年是我最幸福的时光,六个大人宠着我一个小孩,真正“小皇帝”一样。我说要养鸽子,姥爷马上淘换来两只鸽子。人家养鸽子有许多讲究,我养鸽子跟养鸡一样,扎起翅膀不让飞,没几天,大门插关儿在夜里被人拨开,把鸽子偷走了。第二天我哇哇大哭,姥爷有点幸灾乐祸,说“丢了丢了吧,省心”;我说要养蚕,马上就有蚕宝宝,还有大姑提供桑叶;我把奶糖扔在玩具箱里,夏天糖化了,玩具都粘在一起,姥爷一边用大盆洗一边数落我。我记事儿的时候,小姨还在商校读书。她刚工作没多久的春节前,带我到所城里路北的新世界逛街。新世界是一座二层楼的老百货公司,呈“日”字形,中间有两个天井。节前人很多,在玩具柜台前,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男孩儿,把刚买的母鸡啄米玩具掉地上摔坏了,孩子妈非说是我碰掉的,不依不饶,小姨只好赔她钱,把那个铁皮玩具买下来。小姨领着我悻悻地回了家,好在巧手的姥爷把玩具修好了。尽管姥姥与某些邻居有点儿小龌龊,但在德仁里人缘儿很好,大人们尊称她老赵、赵大娘,小孩子随我叫姥姥、奶奶。姥姥是解放脚,大步流星,豪爽热情、乐于助人、嫉恶如仇,不像别的老太太整天围着孙子、锅台转,姥姥经常带我逛街、看电影,甚至带着一群半大孩子上山拾草,去东口子外赶海。姥姥与桑姥姥、郭姥姥是闺蜜,经常互相串门,多半是她去别人家,一边帮着摘菜什么的一边聊天,总有的可聊,总是很开心。我对6号院往外半条德仁里的人家都不熟,也没什么记忆,只有街口的王姥姥是例外,她也是姥姥的好朋友,俩人一见面,姥姥喊她“老白毛儿”,她叫姥姥“赵大脚”。王姥姥两口子没有子女,她老头儿也是一头白发,个儿不高。王姥姥会编花边儿,从街道领来白线,加工后再送回去,挣点手工钱。我跟姥姥常去串门儿,她们聊天,我便目不转睛地看她做活,几个小棒槌儿左右翻飞,一会儿就编出长长一条。其实那就是蕾丝边,当时是烟台外贸出口的主要商品,赚了不少外汇。我姥姥就不会这些细致活儿。有一年夏天给我买了一条新短裤,没有兜儿,而我非要个兜装东西,可能姥爷在忙别的,姥姥就粗针大线给我缝了一个,还不一个色儿,我却很高兴,跑出去到处显摆,大光妈阴阳怪气儿地说了两句,搞得我很扫兴。姥姥家对门2号院有一家姓魏的,也是军属,男的常年不在家,女的独自带一个孩子,姥姥经常去帮她干这干那。那个比我大点儿的男孩儿,冬天穿件咖啡色的小皮夹克,这成了我多年的憧憬,工作后终于自己买了一件。魏家阿姨生二胎时,丈夫没及时赶回来,姥姥把她送去的医院,忙前忙后。孩子生了,医院催促起名字,好登记、报户口,焦头烂额的产妇就拜托赵大娘给起一个。我姥姥也不客气,说:“儿子叫魏克,女儿就叫魏娜吧”。后来不久,魏叔叔转业,他家搬走后,搬来一家有双棒儿的,那俩孩子比我小,特贱招儿,我跟小哥儿俩打过架。那个姥姥给起了洋气名字的小魏娜,如今也年过半百,可能已经做了奶奶或姥姥。2号院还住着高X友一家,他是舅舅的同学,据说学习成绩特好。舅舅转业回来时,这位同学的日子已经过得很不堪了。我对他的记忆是长得有点儿像浩亮,“一边一块疙瘩肉”;还有就是几乎天天喝醉,把会计工作也丢了。起初靠卖血,后来医院不再收他的血,因为他老喝劣质白酒,血液里酒精含量太高。他只好拉大板车为生,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,有点钱就喝酒,喝醉了倒也不闹事儿。记得有一天,对门儿院里院外聚了好多人,还来了警察,原来高的媳妇儿上吊自杀了。听大人们叹息、议论:家里什么粮食都没有,就一点儿豆腐渣,她是真没什么活头儿啦。高的女儿小燕比我小两岁,突然没了娘,爹又整天不着家,只有爷爷带着那孩子。家里没奶、没吃食,爷爷只好让小燕嘬他乳头——当然什么也嘬不出来。姥姥性格外向,心直口快,经常爽朗地大笑。姥爷正相反,虽然脾气倔,但不太言语。老两口儿也闹矛盾,姥爷从来不和姥姥吵,现在想,他是不跟姥姥一般见识,由她去,反正一会儿就没事儿了。姥爷和姥姥的故事可以写本小说,以后再讲吧。我从小跟他们长大,有着极深的感情。姥爷天天推着我出去逛,小木车上水、零食、板凳、雨伞一应俱全,就像一辆小小的房车。每次临回家之前,他总要到德仁里西口斜对面的小杂货铺坐坐。那儿经常会聚几个老头,每人买二两散白干儿,人守一只蓝边白瓷杯,边喝边聊,有时谁带一包花生米,或者买几两猪头肉,便不必干喝,几个老头儿捏着酒咬儿,比平日多了一些快乐。这是姥爷唯一的社交。我很乐意跟姥爷去小铺儿,一是会有好吃的,二是喜欢闻那里的味儿,那是一种肥皂、香烟、糕点、水果、白酒、猪头肉等混合在一起的甜腻腻的味道,是故乡的味道。夏天的晚上如果天气好,姥爷会在屋顶平台挂个蚊帐,我们祖孙俩躺在凉席上,特别风凉。四周是姥爷和姥姥种的花儿,花香阵阵,姥姥喜欢茉莉、栀子等,姥爷则什么都养。有一件事我至今弄不清是梦境还是现实:某天夜晚我和姥爷躺在蚊帐里,看到一大片星星从天空划过,离我非常近,仿佛站起来就能摸着。姥爷告诉我那是彗星,也叫扫帚星。1967年到1970年的某个夏天,有大规模彗星活动吗?冬天烟台经常会下很大的雪。大孩子们打雪仗,或找面没有窗户的墙,堆很多雪,再掏洞,这样底下是个小屋子,上面是滑梯。这些我都只有看的份儿。有几个连狗都嫌的大孩子特别坏,不仅欺负我,还偷偷给姥爷使坏,比如姥爷刚扫完街道,他们故意扔脏东西;他们打雪仗,姥爷怕打着我,拉我回家,他们在后面用雪球袭击他;有一年春节,舅舅给我糊了一个灯笼,雪白的纸上贴着红红的剪纸。吃完年夜饭,姥爷给灯笼点上蜡,带我出去游灯,走到德仁里西头的那个高门台儿,突然窜出几个熊孩子,往灯笼里扔雪球,蜡被砸灭了,我被吓哭了。凡是这种时候,姥爷从来不发火儿,总是默默领我离开。想必我小时候也是个不大讨人喜欢的少爷秧子,姥爷对我却非常耐心。喝腊八粥,我不喜欢里面的花生和豆子,姥爷就讲他小时候,家里穷,平时吃不到大米,腊八能喝上粥,是不得了的太幸福。小哥儿仨都不舍得吃枣和花生,留到最后,他喊一二三,才一齐扒拉到嘴里。 如果天气不好没法出去,姥爷就哄我在家玩儿,画画、搭积木、玩儿玩具,还用椅子、木板、纸箱、煤铲儿给我搭汽车、坦克、飞机,或者做虚拟游戏,如警察与司机,指挥官与飞行员,我对戏剧的感知也许就是从那时候确立的。白天在1号院玩儿、吃饭,晚上姥爷带我去7号院睡觉,睡前给我讲故事,或者下跳棋。妈妈屋子非常空旷,只有少量家具,最吸引我的,是墙上挂的一个黑、红两色细方格的人造革女式提包,里面装着我的零食。抱着那只提包,就像抱着妈妈,有股妈妈的味道。现在看来,姥爷很早就对我进行素质教育,如对人要尊敬、有礼貌;每当我大声说话,姥爷就跟说:这屋子里不光有咱们,还有一些看不见的小精灵,不要吓着它们。好多年后,第一次看《龙猫》时,猛然想起姥爷的话,很是惊讶。姥爷会说流利的日语,早年间他在沈阳皇姑屯火车站当过调度员,再早还在日本裁缝店学徒七年。七七事变前夕,他从日本同事那儿听到消息,假托母亲生病,连夜带着姥姥和才一岁半的我妈仓皇逃回关内。姥姥一提这事儿就气儿不打一处来,“ 都赖小鬼子,我的金戒指都丢了!”姥爷有许多与众不同的习惯用词,比如汤池、邮便所、味之素、幼稚园等。就因为这段历史,“文革”时他没少挨批,桂枝姨的公公带着大光妈等几个街道老头老太太,动不动就开姥爷的批斗会。那时我才三、四岁,每回都被吓得大哭,有一次他们竟把我塞到大衣柜里,所以后来我一直很惧怕狭小且黑暗的空间。姥爷特别讲究卫生,衣服虽旧却总是干干净净,补丁补得整整齐齐;家里家外的地每天扫好几遍,扫街道不知是他自愿的还是“惩罚坏分子”强迫的,反正每天天不亮他已经把整条德仁里扫完了。如果是住7号院,等我醒来,他已经坐在我旁边,等着给我穿衣服,去1号院吃早饭了。夏天,姥爷每天用大木盆给我洗澡;冬天,定期带我去张裕路南的“汤池”。有一年春节前,洗完澡姥爷先给我穿好衣裳,我就跑了出去。大堂里人挤人,正中间是一个烧得旺旺的大铁炉,四面有铁丝围栏圈着,有个比我略大的小姑娘儿,被人挤倒在围栏上,又扑向了火炉,顿时”滋拉“一声……我离着不到两米,人们立马蜂拥过去。姥爷衣衫不整地从男部跑出来,看见吓傻了的我,奔过来拉上我就冲出门。也不知那个女孩儿后来怎么样了,破没破相。“文革”开始时我两岁多,有一天姥爷推着我上街,在二马路转盘西南角长途汽车站遇见游街的,几辆大卡车从马路对面的垃圾库开出来,每辆车的车斗前面站着几个人,戴着纸糊的高尖帽,胸前挂着大牌子,上面倒写着字,打着大红×。现在想想,姥爷虽然挨过批斗,但没有遭受此般侮辱,也算幸运了。记不清舅舅哪年转业的,肯定是在游街和女孩事件之后。舅舅烟台艺校毕业后,考上辽宁公安总队文工团,后调去二炮文工团,是舞蹈演员,曾在大型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中饰演飞夺泸定桥的十七勇士之一。“文革”时二炮文工团解散,正值职业黄金时代的舅舅无奈回到家乡,先在机械模具厂工作,后被抽调去筹建烟台市少年宫,最后又到母校烟台艺校做舞蹈教师。部队文工团的任务是慰问指战员,因此一年中大多时间在各地慰问演出,而火箭兵的驻地和试验基地都在偏远地区。舅舅他们有一次曾在青藏高原连续半年采风、慰问演出,缺氧使得许多人脱发,舅舅也是,他回烟台时,已经开始谢顶了。少年宫建在老动物园里。我离开烟台后,动物园搬到了南山根儿上,老动物园改为花园,并盖了少年宫,还有一座小礼堂。之所以选那儿,可能因为西边紧挨着劳动人民文化宫。现在那里也是烟台的文化中心,从所城里到西南河,是一座横亘东西的巨大建筑,里面有图书馆、少年宫、京剧院、大剧院、文化宫、群艺馆、博物馆。舅舅回家后,我最喜欢听他讲故事。不是所有故事都专门讲给我听的,有些是舅舅给妈妈、小姨或邻居讲,我在旁边蹭听,多半是他看过的“内部电影”,其实没记住几段内容,令我着迷的是他讲的时候声情并茂的姿态。专门讲给我的都是些童话,怀疑是他现趸的,我虽不识字,但有几本童话书。有一天晚上忘了为什么,讲故事、怎么哄我都是哭,姥姥烦了,不再管我,舅舅答应给我画画,我终于睡去。第二天一早,在我枕边放着三幅画:坦克、军舰、战斗机。舅舅结婚后,我还因为舅妈闹过一次失踪。有一次随姥爷逛街回家,他给我买了根奶油冰棍儿,让我坐在南山路小学门口吃完再回去,免得妹妹看见了要,当时她还是个吃奶的孩子。正是下班时间,我吃着冰棍儿想起了舅妈:她也下班了,挺着大肚子,我应该去接接她。舅妈在西边造锁厂工作,油然而生的使命感使得我沿着三马路、东关街、所城里一路走下去。小孩子嘛,路上有什么热闹都凑过去看,一会儿就忘记出来的目的是什么。我记得都快走到毓璜顶了,天已经黑透,于是又往回走。岂不知这两个小时,家里已经翻了天,舅妈根本想不到我会去接她,不可能留意看我。姥姥找遍德仁里所有院子,姥爷、舅舅到附近花园、常去的地方找,听邻居说在三马路一个操场门口见过我,慌忙又跑去找,那里正在挖防空洞,怕我掉进地洞。等我若无其事走回家时,大人们和一些热心邻居正商量着要去派出所报案呢。说起防空洞,这是中国除大炼钢铁之外另一件荒唐之极的事情。在“深挖洞”的号召下,全民人民都行动起来,那阵子到处都是土坯,我还跟舅舅去拉过土脱土坯呢。姥姥家院子很小,也在无花果树底下挖了一个比方桌大不了多少的洞口。可是烟台地下水位高,挖不到两米就出水,家家户户院子里都有个大水坑,冬天还不能当菜窖,人们只好往里填炉灰。在父亲的强烈要求下,我曾短暂地上过三个月幼儿园,但在我锲而不舍的哭闹下,姥爷终于怒了,“不去幼稚园了!” 不过那短短三个月,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蛮深的,比如老师不知真假的忆苦思甜,我带头哭得最惨,大得老师赞许;每次中午吃包子,都会发动我们剥蒜;养成了自己洗手绢、袜子的好习惯,一天洗三遍,生生把一条崭新的小手绢洗褪了色;用绿、白花纹相间的小搪瓷饭碗喝牛奶,有股特殊的味道;和小朋友用杨树叶梗拔根儿,要先在鞋里沤;幼儿园也挖了个大防空洞,好在没挖出水,老师让我们所有小孩儿到拱圈上用方木块夯土。最难忘的是幼儿园的葡萄架和老洋楼,我们背着老师揪藤蔓嚼,酸酸的。后来听姥姥说,那座方方正正的洋楼北边,靠海的一座洋楼,是她小时候的家。姥姥是广东人,十来岁被养父母带到烟台,她养父是烟台海关官员。现在的烟台海关大楼在张裕公司与市府街之间,不知老海关官署在什么地方。(请参阅《疑是天使》)姥爷算是有文化的人,但他只带我逛街,也不爱串门儿,看电影、看演出(文革时期有许多汇报演出,无非是语录歌、忠字舞、样板戏什么的)都是姥姥带我去。离我们最近的是南山路的东风影院,基督教奇山礼拜堂改的,文革后又改回教堂,东风影院搬到了二马路转盘的东南角,就是原先垃圾库的位置,还有新世界、新中国影院和市府礼堂。一个小城市有这么多影院不算少了,但那时电影并不多,我甚至都没记住看过什么,也许放电影的时候我都睡着了。但有一件事印象特深,那时放正片前要放加片儿,一般都是“新闻简报”,新闻简报一般都是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宾,而中国亚、非、拉的朋友特多,一见毛主席与黑人朋友亲切握手,我就吓得钻到姥姥怀里,把耳朵也堵上,好像黑人说的话也很恐怖。好多年后,姥姥还拿这事儿开我玩笑。

从烟台山的灯塔上俯瞰大半个烟台市。沿着海边的是海岸街(摄于1990年8月20日)


南山路与二马路十字路口的小理发馆依然还在,小时候姥爷经常带我到那儿理发(摄于1991年9月30日)

以前自来水没通到各家院子里时,每条街道都有这样的公共自来水井。姥姥家门口也有一个,供整条德仁里的居民用水。每天早、晚担水高峰是一景儿,也是邻居们相互打招呼的时机(摄于1991年9月30日)

烟台盲哑学校的学生们在打篮球。这组盲哑学校,以及烟台SOS村的照片,发表在《瞭望》杂志海外版上(摄于1991年10月8日)

再次回烟台,南山路的东沟路和三条里已经改建成“民生小区”,路也拓宽了许多。我站的地方就是原先德仁里的口上(摄于1993年9月)

站在我曾上过的幼儿园门口。里面的样子与小时候已完全不同,那座小洋楼也拆掉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特难看的灰色水泥楼——国旗后面露了一角(摄于1993年9月)

烟台西炮台。东炮台在海军炮校东边,那边还有清末烟台海军学校的旧址(摄于2000年10月)
从新世界顺着胜利街往北走,穿过市府街就到了北马路,往东一拐便是朝阳街口上的新中国电影院,朝阳街北端就是烟台山,新世界和朝阳街是老烟台两个繁华的商业区。市府街是与北马路基本并行的一条东西向街,东起张裕门前解放路。舅舅筹建少年宫时,办公地点就在市府礼堂旁边的一座小木楼上。原先在市府街东口儿有个食品店,四婶就在那儿工作。四叔、四婶是经我妈妈介绍认识的,见了一面后,四叔又主动跑到人家单位去找,四婶一见有点不好意思,四叔竟对着四婶说:”我找XXX“,弄得四婶不知所措。脸盲症是家族遗传吗?不知我爸有没有脸盲症。四叔结婚后住所城里,离四婶娘家隔一条马路。四婶姓朱,父亲以前是渔民,后来做了烟台渔业公司的党支部书记。朱家姥爷体胖心宽,爱喝酒、爱大声说话,也非常好客,我们两家走动得比较勤,我经常跟姥姥去串门。我家一直是在堂屋的矮桌上吃饭,坐小板凳,所以我从小不会盘腿。朱家是大炕,在炕上吃饭,这成了我每次去最头疼的问题,细心的姥爷便准备两个枕头让我坐。朱家姥爷一喝酒就爱讲以前的事儿,说以前他们出海打鱼,只带米和淡水,打上来的带鱼,用海水洗净,米饭做好了再把带鱼段放在米饭上闷着,菜和饭就都有了。他有个本事,把一块带鱼放到嘴里,一边说话一边往嘴里扒饭,一会儿吐出一根整鱼刺。朱家姥姥颠着小脚忙前忙后,一个劲儿劝客人“逮吧,快逮,多逮点儿”,她做的山东打卤面尤其是一绝,现在想起还流口水。后来,我每次回烟台都要去看望朱家姥姥,姥爷已经不在了。我爸在北京,我妈又是媒人,所以这个四弟便经常去东边我姥姥家,看有什么力气活儿需要干。有一次四叔来家里,我正在打苍蝇,再用姥爷给我做的竹夹子把死苍蝇夹进一个小瓶里,见四叔来了,把玻璃瓶举到他面前炫耀战果,四叔一个劲儿地说“不简单、不简单”,我才第一次知道,夸人不一定直接说“好”、“棒”,还可以说“不简单”、“有水平”。四叔也很不简单,我亲眼见过他用木头和帆布做的卷烟器,虽然个头跟板儿砖那么大,但原理与现在那种小巧的卷烟丝器一样,卷出的烟卷儿也倍儿漂亮;他还给我做过一个万花筒,与卖得一样,只是粗一些。四叔是动物园的兽医,他本来就是学兽医专业的,但不知为什么这之前却在化肥厂工作。化肥厂在西郊,很远。有一次我跟四叔到他们厂子玩儿,午饭他给我买了一个猪蹄,我啃得干干净净,四叔逢人便说“我侄子一个人能啃个大猪蹄子,太有水平了!”那个猪蹄五毛钱,是四叔三、四天的菜金呢。

烟台所城里的老房子,四婶娘家就在这附近(摄于2000年10月)

海滨城市住宅的窗户外面都有一道木窗扇,以防台风(摄于2000年10月)


沿着大马路,有许多这样的小街通往海边(摄于2000年10月)

朝阳街附近,现在还有一些这样的老房子(摄于2000年10月)

这个时候,海岸路虽然也拆了一些老房子,但大体格局如故(摄于2000年10月)
转载声明:本文转载自「西局书局」公众号,搜索「xijushuju」即可关注,[ 阅读原文]。 |  |Archiver|手机版|小黑屋|烟台前线
( 冀ICP备13012704号-1 )业务客服:
|Archiver|手机版|小黑屋|烟台前线
( 冀ICP备13012704号-1 )业务客服: